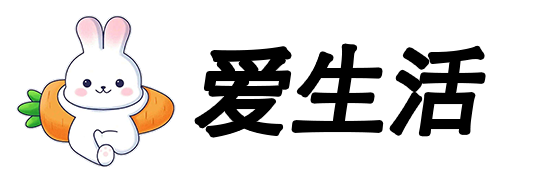
本文转自:右江日报
春分时节轻暖轻寒,万物复苏,正是赏花赏春、育苗插秧和植树造林的好时光。
这个时候,接收到家乡草木的召唤,我乘着一缕古典的月色回到故园。
村里村外水波潋滟,蛙声如鼓。春风里,绿树翠竹亲吻着厚土,草木的气息一遍又一遍地荡涤着我那狂躁的心。
村头尽是漫无边际的油菜花。缕缕霞光穿透迷雾铺洒在一垄垄金色的田地上,油菜花与往年一样坚定着自己的信念,在这布满晨露的时光和沉甸甸的梦醒时分,尽情地分享着春分时节的明媚。
细雨绵绵,雍容峭拔的松木、香椿树密密麻麻地立在小山村东边的山坡上,俨然生成铺天盖地的绿涛。在郁郁葱葱的起伏里,镶嵌着一座座粉墙黛瓦的小楼,我的父老乡亲们就在这些小楼里居住。年复一年,他们穿梭在小楼和树木之间。在层层叠起的草木里,我常常沿着蜿蜒的村道攀上迤逦的山峦。
我想,久远的年月里,我的祖先在这里栽下第一棵树时,也种下了祈愿。我曾多方寻访,试图知道是什么年月、什么人、从什么地方来,在这偏僻、荒凉的山脚下种树安家。据说是在一个春分时节,第一批先祖来到这里,除了在山村东头种下松木、香椿树外,还在小山村四周各植下一棵榕树,说是用榕树封村,永保山村的安宁。不知过了多久,不仅是山岗上的松木、香椿长高,村四周的榕树也都遮天盖地了。童年的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在这些大榕树下嬉戏。
因我小时候体弱多病长不高,父母挑了良辰吉日选择在村南边的榕树旁种下了一棵香椿树,说这是我的生命树,在这棵榕树旁边种下它是为了托大榕树的福,如今这棵香椿树早已亭亭玉立。遗憾的是,几年前,村南边的这棵榕树因为太老,主干无风无雨而自己倒下。村老们率全村男女老少,杀猪宰牛,烧香跪地,祭拜倒下的榕树。
每到惊蛰、春分时节,山村的西边漫山遍野的桐花开得如火如荼。这些桐树有的是先辈们种上的,有的是后来自行繁衍的。我站在高坡上,看到一棵棵桐树盛开着淡紫色或是白色的花朵。花朵雪花般地压着枝条,在灿烂的春光里和着树的影子摇曳。我家门口的那棵桐树,这些年一直得到阳光雨露的滋润而越长越高大。现在它开满紫色花朵的树冠尽情地舒展着,那熟悉的、淡淡的芬芳弥漫着家园。我一直在想,在自己的一生中有这么一棵桐树相伴是一件多美的事情啊!
树的年轮与叶脉里,镌刻着家乡人“树养人丁水养财”“春三月山林不登斧,以成草木之长”的传统意识和“春分种树南坡下”习俗,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在水边岸上、路旁山坡栽植树木。于是绿竹迎风,山路旁尽是长长的树廊,春天玉兰花开,秋天八角、茶果飘香,村庄四季飘逸的全是树木的芬芳。“绿树村边合,青山郭外斜”是山村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。在这里,我找到了宁静淡泊的心境,疲惫的灵魂得到了休憩,浮躁的心绪归于安宁。
家乡民间遗存的风俗里,无论建屋,还是人的出生、成年,乃至死亡、扫墓,都有植树纪念的习惯。于是村里有“添丁山”,山上葱郁,直接彰显着家乡的人丁兴旺。村里人建屋,须事先向村里提出申请,得到批准后才能去山中砍伐树木,而新屋建好了就在房前屋后或者山上栽种好树好木,既是庆祝新屋的落成,又补栽了树木。当年我爷爷过世在山上埋葬,爸爸率我们栽植了六棵橡树。每到清明,伫立橡树下,我的心里常常流淌着丝丝敬意。
“二月惊蛰又春分,种树施肥耕地深。”“夜半饭牛呼妇起,明朝种树是春分。”我的父老乡亲遵循季节的秩序,不畏艰辛地耕田耕地种树,“上山植树,下山种稻”,家家种树,家家有树。这样的习俗不知道是从哪时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。去年冬天,父老乡亲在自家的山地里、荒坡上,每个劳力一天挖上百个树坑,手心布满了血泡。今年惊蛰、春分一到,大家把一捆捆树苗扛上山,山上山下尽是欢声笑语。
春分,山间草木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