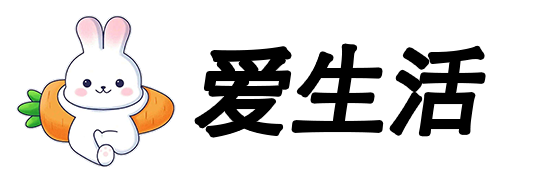
本文转自:黑河日报
一手烟火 一手诗意
□何丽晶
清晨给绿萝浇水,看阳光在叶片上跳跃,忽然懂了汪曾祺笔下的“一手烟火一手诗意”。
这位被誉为“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,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”的老先生,以为最美的日子“当是晨起侍花,闲来煮茶,阳光下打盹,细雨中漫步,夜灯下读书。”他说:“在这清浅时光里,一手烟火一手诗意,任窗外花开花落,云来云往,自是余味无尽,万般惬意。”
在汪曾祺笔下,生活中的诗意更具象化了。一杯青瓷里的香茶,一个侍弄花草的清晨,一个暖阳下打盹的午后,一本引人入胜的好书,一把细雨下的油纸伞……这般寻常岁月,经他笔锋点染,竟生出“竹炉汤沸火初红”的意趣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,最本真的诗意原来不需要踏雪寻梅,生活本身便是流动的诗。
古人早已深谙此道。陶渊明脱去官袍扛起锄头,在豆苗稀松的田埂上遇见南山;李白在寻常酒家里挥笔,让桃花潭水成了千年情义的刻度;王羲之与友人在山间饮酒,曲水流觞之间写下的《兰亭集序》竟成了永恒;而《红楼梦》里的小儿女们,采菊作诗、煮茶论道,硬是把深宅大院的日子过成了诗笺上的浪漫。
现代社会里,手机常把我们的眼睛困住,指尖滑动间,多少诗意湮灭在时代的洪流里,却仍能在缝隙里生长。春晨市井街道上,留心迎春花在枝头巧笑盼兮的姿态;夏夜乘凉时,听孩童追逐欢笑洒下的幸福;深秋扫落叶,把满地金黄卷成岁月的书简;冬日围炉夜话时,耐心地等一场大雪在窗上描画出好看的窗花。正如余秀华在麦浪里拾取疼痛的诗句,房车旅人在车轮上书写流动的篇章——诗意从不拘泥形式,它可以是酸梅汤里漾开的胭脂色,也可以是手工布偶衣襟上歪斜的针脚。
最深长的诗意,往往蛰伏在最朴素的烟火里。老母亲离别时的唠叨与叮咛,归家时那盏守候的灯火,爱人宿醉后凉在床头的醒酒茶,你的小儿女出其不意地在你脸上啄出的亲昵,都是生活馈赠的绝句。
当我们在菜市场挑选带着泥土的萝卜白菜,在厨房熬一锅咕嘟响的粥,把旧毛衣拆了织成坐垫,在旧书摊邂逅泛黄的诗集,那些细碎的光亮便自动聚成诗句。正如汪曾祺所说“美,多少要包含一点偶然。”而我们要做的,不过是在烟火日常里,多留一份驻足的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