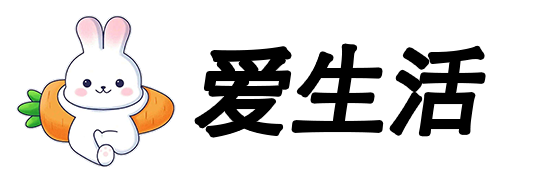
在新疆第一次喝卡瓦斯人就快不行了。
偌大的烤肉摊子,我竟表现得像弃儿一般无助,忍不住想要再喝一口,可又想永远留在第一口给我带来的感动与彷徨中。
当失明的野狗第一次看见彩虹,它开始说话;当没壳的甲鱼长出翅膀,它挺直了脊梁;当南方人第一次喝到卡瓦斯,他写下了这篇文章。
卡瓦斯很特别,当你轻抿一嘴卡瓦斯,当那股带着些许粘稠的液体滑进你的口腔,啤酒花的清香与蜂蜜的回甜就同时涌进了你的脑海,它太甜了,以至于能让你再度想起当年那个在梦巴黎包间独自啜泣的女孩。
她失去了冠冕,但依旧是女王。
与市面上那些娘娘腔汽水不同,卡瓦斯没有前调与后调,它不需要,它只有如大口径舰炮般强大的甜,也许还带着一点啤酒特有的顽皮的苦涩。
它像蜂蜜也像啤酒,像鲜花也像土壤,它普通又不平凡,廉价又遥不可及。它随处可见,却又在离开后无迹可寻。
喝卡瓦斯,你就要习惯于这种过于直白的味蕾刺激,更要习惯让甜蜜的岩浆冲刷舌苔覆盖下的味蕾。
它是勇敢的拳手,是愤怒的公牛,是顽强的士兵,当你真正喝完一杯卡瓦斯,你也应该流下了热泪。
事实上,卡瓦斯与东北的格瓦斯系出同源,都是当年俄罗斯人带来的爽饮。
但不知是哪位仙人改良了原版配方,在其中加入了蜂蜜,并用谷物取代了黑面包作为发酵物,从此与格瓦斯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。
我是在烤串摊子上喝的卡瓦斯。
但与其说是喝卡瓦斯,不如说是工蜂宿醉之后直接在我嘴里拉了一坨醉蜜,带着一股子气泡,经过咽喉的上下其手后,最终流向了我的十二指肠。
卡瓦斯让我的舌头同时体会到了甘甜与苦恼,而唾液则化作了舌头流下的泪。
我也仿佛听见舌头说它要离开了,它要去找寻一场无悔的爱情,可能就在南方以南。我说也罢,你走吧,大不了从此装聋作哑。
人们可以在新疆的绝大多数餐馆点上一杯卡瓦斯,就像要上一份抓饭那样简单。
哪怕是在远离乌鲁木齐的北疆,在距离克拉玛依两百公里的某个小镇上,你也能点上一杯冰凉醇正的卡瓦斯,即使那里的丁丁拌面可能连洋葱也没有。
卡瓦斯早已经变为了当地人生活中的一部分,成为了一颗猛烈旋转的构造西北生活的齿轮,新疆不能没有烤肉与西瓜,当然也不能没有乌苏与卡瓦斯。
下班之后,点上几串肉筋与烤肉,几个烤包子,弄点醋,再要上一杯卡瓦斯,然后看着天山山脉的轮廓逐渐消失于远方,直到眼前只剩下一轮孤寂的夕阳,买单,离开。生活就是这样简单。
我的新疆朋友告诉我,卡瓦斯得喝桶装的,而且必须是那种宛如盛放化工原料的塑料桶,每天由当地的厂家配送至店里,桶身大多布满划痕,似乎与塔里木盆地度过了同样厚重的岁月。
你要喝,老板就熟练地扭开桶身上的龙头,就像是给你倒了一杯石油。
卡瓦斯又是最被低估的新疆特产,外地人听见卡瓦斯三个字,第一反应通常会认为这是某个行吟诗人,或是某个流浪歌手的名字。
你能在大理的玉石店买到和田玉,或是在成都吃到算是正宗的馕坑肉,每个酒吧也都有喝不完的红瓶子乌苏,但卡瓦斯总是被忽略,似乎外出开店的新疆人都不想让别人知道卡瓦斯的存在。
实际上,这并不是新疆人金屋藏娇,因为桶装卡瓦斯的保质期通常只有三天,三天够干什么,路上堵的话,说不定三天还没出新疆。
“新疆太大了”,乌鲁木齐烤肉店的老板对我说,“以至于这么多年,我仍未见过喀纳斯湖的日出。”
“但你却喝上了一杯卡瓦斯。”
如今我很想告诉他,卡瓦斯也走出新疆了。